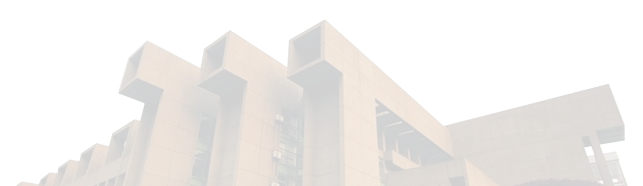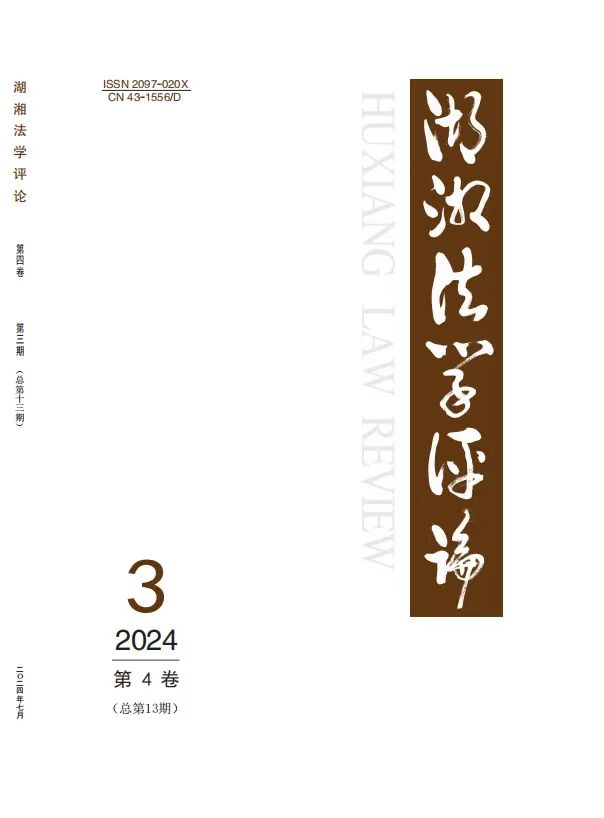
本文发表于《湖湘法学评论》2024年第3期(总第13期)“学术专论”栏目
【作者】徐国栋,法学博士,厦门大学法学院南强重点岗位教授。
【摘要】继《奥地利民法典》于1988年采用动物非物的规定后,2000年的《阿塞拜疆民法典》第135条第3款采用了植物非物的规定,两者配合,开启了非人类生命去客体化的思潮。1992年的《瑞士宪法》第120条赋予植物尊严权,也是这一思潮的体现。阿塞拜疆和瑞士的规定建立在非人类生命界的去动物中心主义的成果上。为了提高植物的法律地位,学界进行了大量的植物有智力的论证。实际上,这种论证并非植物获得主体资格的基础,其基础是植物的良好生存代表的生态利益,所以应采用法益实体说来证成植物的主体资格。植物的主体化挑战人类的食物权,可通过把植物分为自由植物和孤立植物来解决两种需求的矛盾。孤立植物可以为人所用,但不得浪费,并且要带着尊敬享用。如果承认植物的尊严权,我国《民法典》承认的植物新品种权的正当性将面临挑战,同样受到挑战的还有我国《宪法》在国有自然资源权框架下作出的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的规定。在宪法生态化的思潮下,此等规定应在调整为也包纳其他权属下的动植物后与我国《宪法》关于国家保护环境的责任的规定合并,并增加禁止对动植物实施任意的基因操作的规定,由此实现动植物的主体化。
【关键词】植物非物;植物智力;植物的尊严权;《阿塞拜疆民法典》;植物的宪法地位
一
从动物非物到植物非物
1987年11月25日,海因茨·费舍尔(Heinz Fischer,1938—今)和沃尔特劳·霍瓦特(Waltraud Horvath)两位议员向奥地利议会司法委员会提出议案,建议在《奥地利民法典》第285条新增如下附加条:“1.动物不算作物;它们受法律的特别保护。2.适用于物的规定仅在没有不同和特殊规定的情况下才适用于动物。”奥地利议会收到这个议案后,在1988年3月3日的会议上讨论,通过票决,在修改后把上述建议转化为立法。现在的《奥地利民法典》第285a条曰:“动物不是物;它们受特别法保护。适用于物的规定仅在没有不同和特殊规定的情况下才适用于动物。”海因茨·费舍尔及其同事的提案理由是:在一条狗与一块砖之间没有法定的区别是不合理的。此语是对传统民法客体理论不区分生命物和无生命物的深刻批判,但批判得不彻底,因为在一块砖与一棵树之间没有法定的区别也不合理,狗和树按照生物学都属于生物,所以,费舍尔未把自己开启的问题进行到底,提出植物非物的修法建议。之所以如此,还是因为狗在受到侵犯时会叫唤,而树不会,这正应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这句话。令人欣慰的是,费舍尔未做的事情,12年后的2000年由《阿塞拜疆民法典》第135条第3款做了,它规定:植物和动物不是物。它们的法律地位由专门法律确定。如果立法无专门规定,物的法律身份也适用于植物和动物。这是人类第一次在民法典中规定植物非物,而且把植物非物问题放在动物非物问题之前规定,这样的排序允许人们推断前者比后者更重要。确实,前者的数量要成倍地多于后者。至此,立法者在民法中把有生命物区别于无生命物的意图基本得到贯彻。说“基本”,乃因为生命物除了动植物,还有真菌、微生物等,暂无立法者以明确的规定把它们排除出客体的行列,尽管在2018年,蓝蝴蝶公司(Compagnie des Papillons Bleus)提出的《国际树木权利公约》草案第7条要求公约的签字国保护大真菌(Macromycètes),此条让真菌的法律情势问题在法律文件上现身,但未提议大真菌的主体化。
《阿塞拜疆民法典》第135条第3款在思想史上的意义如何?马修·霍尔(Matthew Hall)概括得好:《圣经》的一些段落可以说考虑了动物并指出了人与动物之间的一种可能的横向关系,但几乎无证据表明《圣经》曾赋予植物这样的考虑。此语说的是在非人类生物界研究中存在的动物中心主义的起源。从这个角度看,《阿塞拜疆民法典》第135条第3款是对这种主义的挑战。
顺便指出,与西方贱视植物的传统不同,印度的耆那教比较正视植物在非人生命体系中的地位。该教认为,生命体有触觉、味觉、嗅觉、视觉和听觉五种感觉。宇宙中所有的生命体都按照其所属的感官的多少来分类。最低级的生命体仅有一种感官,即触觉感受器官,植物属此;最高级的生命体拥有所有五种感官,人类和大部分动物属此。其他中间性的生命体要么有触觉、味觉两种感觉,蚯蚓属此;要么有触觉、味觉及嗅觉三种感觉,虱子属此;要么有触觉、味觉、嗅觉和视觉四种感觉,蚊子属此。这些说明见证了耆那教也贱视植物的一面,说它们是最低级的生命,但如下说明见证了该教对植物看法的另一面:禁止食用在地下生长的蔬菜和水果(根茎植物),理由是为了取得这类蔬果,人们须连根拔起植物,如此就毁坏了整个植物,并且破坏了其根部附近的微组织。此外,该教只许在果蔬自然成熟并准备落地时才可采摘,或者等它们从树上掉落后才采收。如此可享用植物而不害其性命。如果要从树上直接采果,只能采摘必要的数量,不能浪费。谷类如小麦、稻米、玉米,以及豆类等,要在作物或豆荚已干燥且死时才能采。绝对禁止为了取得木材或作其他用途而砍树。总之,耆那教禁止信徒在超出个人需求的情况下任意“杀戮”植物。
让我们回到奥地利。《奥地利民法典》的上述规定开创了重设动物民法地位的动物非物模式,受到《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阿塞拜疆民法典》《摩尔多瓦民法典》《爱沙尼亚物权法》《加泰罗尼亚民法典》的追随。在学说上,上述规定引发了大量的研究。就中文世界而言,标题中包含“动物不是物”字样的论文有3篇。但《阿塞拜疆民法典》的上述规定已诞生24年,却未发现有哪一部民法典追随其而创立“植物非物”模式,除了一位秘鲁议员为了证明在该国民法典中补立“动物非物”之类的规定的必要性而援引了上述规定,别无其他援引。在学说上,暂未发现任何专门研究。这可能是因为阿塞拜疆的国际地位不如奥地利,也可能是因为该国使用的阿塞拜疆语不如德语通行,这两个不利因素影响了《阿塞拜疆民法典》的这一出色规定扩大影响。本文拟介绍这一规定的古今思想基础以及类似的立法或提案,从而为植物乃至全部自然物的主体化张目。
二
植物非物,是什么?
大哉问!《奥地利民法典》第285条附加条曾经受到类似质疑,终于催生了2012年的新《捷克民法典》第494条的规定:活动物作为有感生灵,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价值。活动物不是物,关于物的规定仅在不违背其本性的范围内类推适用于活动物。此条终于正面说清了动物是有感生灵。所谓有感生灵,是能感觉、察知、反应,有快乐感和痛苦感的动物。把动物界定为有感生灵,拉近了它们与人类的距离,因为人类也有苦乐等感觉,按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人类就要善待动物,甚至赋予其有限主体地位。
读者可注意到前段中的两个词,第一个是“它们”。我们从小就在语文课堂上知道,这个第三人称代词应用来指称无生命的客体,现在确认了动物是有感生灵,再用这个词指称动物就不合适了,所以,有必要重用刘半农创造的“牠”字指称动物。当然,如果证明了植物也有生命,更需要创立一个新的第三人称代词指代之。第二个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的“人”,我们不得不用此词来表征动物乃至植物,反映了我们身处的人类中心主义语言学现实。我们的语言以人类为唯一的主体,对于其他存在,只能用拟人法指代。如果我们进入一个生态中心主义的社会,人类将和动植物平等,那时候,人称代词系统也将面临变革。
2009年,以《植物对话:偷听植物世界的秘密》(Pflflanzen Palaver,Belauschte Geheimnisse der botanischen Welt,2008)一书的作者弗洛里安·凯什兰(Florianne Koechlin,1948—今)为首的15位德语学人签署的《发现植物:关于植物权利的莱瑙论文》对本节标题提出的问题作出了回答。其辞曰:植物是生物(德文为Lebewesen;英文为living being)。这一回答好生令人失望,因为植物是生物,从生物学诞生起就无人否认过。生物学研究的对象有三:动物、植物和真菌、微生物。如果这样回答,根据《阿塞拜疆民法典》第135条第3款提出的问题,可得出该款不过讲了一个世人皆知的常识,故为无甚意义的结论。
无独有偶,1994年在法国诞生,由法国树木协会主席、巴黎第七大学教授乔治·费特曼(Georges Feterman,1952—今)起草的《树木权利宣言》(Dé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 arbre)第1条也局部地回答了同一问题。说“局部”,因为它只回答了植物中的一种,即树是什么的问题。它规定:树木是固着的生命体,以相当的比例占据着两种不同的环境,即大气和土壤。土壤中的根系可以吸收水分和矿物质。树冠生长在大气中,可以吸收二氧化碳和太阳能。因此,树木对地球的生态平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条的第一句也令人失望,不过基本复述了树是生物的常识。说“基本”,因为它加了“固着的”定语,树因根而生,不能移动,移动即影响其存活。此条的其他文句,一讲了树木的“跨界”(地上和地下)生存方式;二讲了其生态贡献。只能认为此等贡献是树木应被赋予权利的理由,不似动物因为其有感觉而应被赋予权利的理由。
实际上,立法者宣称植物不是物的理由是我们人类对它们认知不够,如果对它们乱加干预(包括转基因干预),可能造成无法控制的后果,所以,人类应顺应植物的自然。上引《发现植物:关于植物权利的莱瑙论文》说明了这一点:我们对植物的感知能力所知甚少。细胞和分子生物学证明了它们似乎有感知能力,但到目前为止,仍缺乏完整的证据链。声称植物没有感知能力且感觉不到疼痛与相反的说法一样具有推测性。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科学地理解植物的本质。这方面存在认识论上的限制。
既然人类对植物知晓不够,只能抛弃干预植物的生命以达成自己目的的想法,顺应植物的自然。此等顺应体现为赋予植物6项权利。其一,生殖权,绝育技术和其他不育方法的唯一目的是使农作物获得最大的产量,违反了此权;其二,自主权(独立权),植物不是客体,不应被工具化并随意控制;其三,进化权,即植物调试自己适应环境的权利,为此要保持物种的多样性和基因的多样性;其四,作为种的幸存权,即要保障所有品种的植物(徐国栋按:此语应包括所谓的“有害植物”)都能幸存,实现生物多样性;其五,在研究和开发中的受尊重权,即要求研究者和有关工业能感知目标植物的独一无二性,带着尊敬的态度研究之,不得无限制地把植物作为使用客体;其六,排斥专利化权,此权肯认植物并非发明,任何植物的存在都不能仅归功于人类活动。因此,不仅应出于社会经济原因拒绝植物专利,而且应为植物本身而拒绝之。此权的反对目标是植物新品种权。
上述6权的相对人似乎并非普通的植物所有人或占有人,而是植物的研究者和植物产品的开发商,所以,这6权依托的规范并非民法规范,而是科研-开发伦理规则。这一规则体系不同于关于动物的规则体系,后者是地道的民法规范,考虑的规制对象是动物的所有人或占有人以及广大的第三人。
那么,弗洛里安·凯什兰等德语科学家为何要为植物的研究和开发设置上述限制?4位法语科学家(佩尔特、马祖瓦耶、莫诺、吉拉尔东)合著的《植物之美》回答了此问题:人类发展到今天,已有意无意地破坏了地球上植物原有的自然分布状况。许多植物在任意筛选种植和改良后甚至已与其原生种类毫无相似之处。这在农作物上表现得尤其明显:为了片面增加产量而不断选种和改良品种,致使多样化品种逐渐被单一品种替代,或者说许多老品种被单一的新品种所替代。同时,我们还正在自作聪明地对农作物进行冒险的基因实验,而今天任何人都不可能评估此举的长期后果。人们移动了生态效应链,而这一点是人们所不熟悉的,也是不能很好控制的,自然有必要格外小心。仅凭人类目前所具有的知识与智慧,还远远无法将植物界的奥秘穷尽。毕竟植物已在地球上繁衍了上亿年,而人类对植物的系统研究则仅有300多年。绠短汲深,人类还是不要冒进为好。
拟回答本节标题提出的问题当作总结:植物是我们认识不足的对象,少知多畏,我们不能以科研的名义乱加干预。
三
瑞士把植物权利当作宪法问题
1992年,瑞士通过全民公决修宪,新立第120条(非人类领域的基因技术),行文如下:1.应保护人类及其环境免受基因技术滥用的影响;2.联邦应就动物、植物和其他有机物的生殖和遗传物质的使用制定法律,在这样做时,应考虑到被造物的尊严以及人、动物和环境的安全,并应保护动植物品种的基因多样性。
此条的条名和第1款就揭示了确立动植物和其他生物的权利旨在限制基因技术的滥用。此条第2款首先把动植物和其他生物免受基因技术滥用的影响当作瑞士联邦政府的责任而非普通民事主体的责任;其次以宗教术语“被造物”统称动物和植物,并赋予它们尊严权;最后把主体(包括人和动物)和环境的安全、动植物品种的基因多样性的保护当作规范目的。这里的“其他有机物”至少应包括微生物,如果这一推论成立,则第120条在人类立法史上第一次把微生物作为权利主体考虑。
此条中的“被造物”的术语具有宗教性,因为根据《圣经·创世纪》的记载,上帝用6天造世间万物。第3天造植物(青草、菜蔬、树木);第5天造动物(水中生物及天上飞鸟);第6天造人。人、动物、植物三者,通称为被造物(creature)。按瑞士当局的解释,被造物包括动物、植物、真菌和微生物在内。人之所以被排除,乃因为第119条对其有专门规定:1.人类应被保护以防止辅助性医疗生殖技术和基因工程的滥用。2.联邦应就生殖和基因物质的使用制定法律。在此方面,联邦承担对人的尊严、人格、家庭的保护并遵守以下原则:(1)禁止任何形式的克隆以及对人类生殖细胞的基因材料和胚胎的干预。(2)非人类的基因遗传和生殖遗传不得被移植到人类生殖遗传领域或将二者混合。(3)只有在有不育症或避免传播严重疾病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辅助性医疗生殖技术,但是不得为生育具有某些特征的儿童而进行研究;体外受精只有在法律允许的条件下才可使用,且唯有在一定数量的卵细胞能立即被植入体内时方可进行体外受精直到胚胎期。(4)禁止捐赠胚胎和所有其他形式的代孕。(5)禁止人类胚胎和胚胎制品的交易。(6)非经本人同意或根据法律规定,不得对个人的遗传基因进行分析、记录和交流。(7)每个人均有权了解有关自己的直系亲属的资料。此条与第120条平行,目的在于限制人工辅助生殖技术和基因工程滥用于人类,以保障人的尊严。这样,人的尊严和其他被造物的尊严就结伴受到保护。两种尊严被统称为生物的“尊严”。“尊严”指的是此等生物的内在价值,即它们为自身而存在,而不考虑它们对任何人或任何其他事物的有用性的价值。“植物”与“人”的这种结伴性是瑞士立法机关造就的。第119条的草案最初由一份消费者杂志提出,联邦议会在把它加工为法律文本的过程中提出补充,增加第120条作为公决内容。显然,瑞士立法机关认识到了人的尊严与其他被造物的尊严的关联性和同质性,故安排把它们一并规定。这样的安排为我们理解第120条提供了帮助,因为我们通常明了对人的生殖和基因进行操作的伦理风险,却对植物等生物进行同样的操作的伦理风险不敏感,把两者并列规定,可加强我们对后种风险的敏感性。
至此可见,第119条和第120条的目的是禁止鲁莽的基因工程,瑞士人认为这是危险的,所以设定了人的尊严和生物的尊严来对抗权力的傲慢。瑞士人认为,每一次新的基因合成引入都无异于玩生态轮盘赌,也就是说,虽然只有很小的机会引发环境爆炸,但如果真的发生,后果可能是雷鸣般的和不可逆转的。为了合理运用基因技术,瑞士于2022年1月颁布了《联邦非人类基因技术法》(Bundesgesetz über die Gentechnik im Ausserhuman-bereich)。该法与2011年颁布的《联邦人类研究法》(Bundesgesetz über die Forschung am Menschen)形成配合,调整两个领域的基因技术适用实践。《联邦非人类基因技术法》第1条(本法目的)规定,本法旨在:“1.保护人类、动物和环境免受基因工程的侵害;2.在基因工程的应用中为人类、动物和环境造福;3.在此背景下,本法的目的尤其在于保护人类、动物和环境的健康和安全;……5.尊重被造物的尊严……”本条第2款表明了立法者并不完全禁止运用基因技术的立场。第5款重申了尊重被造物的尊严是运用基因技术的前提条件。第8条(尊重被造物的尊严)第1款规定了何以构成侵害被造物的尊严:通过基因工程技术对动植物的遗传物质进行改造,不得损害生物的尊严。如果物种的具体特征、功能或生活方式受到严重损害,并且没有任何值得保护的利益可以证明这种行为是正当的,那么这种尊严就会受到侵犯。要根据动物和植物的不同来评估伤害。同条第2款规定了为达成特别值得保护的利益,可以损害被造物的尊严,这些利益有:(1)人类和动物健康;(2)确保充足的营养;(3)减少生态偏见;(4)维护和改善生态生活条件;(5)在经济、社会和生态层面对社会具有实质性效用;(6)知识的增加。当然,按第3款的规定,联邦委员会可决定在何种条件下允许在利益不平衡的情况下对遗传材料进行特别的修改。此法值得注意的方面是不把被造物的尊严设定为绝对,可以为了人的利益以及非人类动物的健康利益牺牲此等尊严。
《联邦非人类基因技术法》并非无牙之虎,违反该法者,要承担《瑞士债法典》第42~47条、第49~53条规定的损害赔偿责任。严重的,要承担该法第35条规定的刑事责任:三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由此,瑞士形成了保障植物权利的法网,它由《瑞士宪法》《非人类基因技术法》中的相应规定构成。这是一条公法的路径,不同于《阿塞拜疆民法典》第135条第3款的采用的私法的路径。
四
阿塞拜疆和瑞士的规定是破除动物中心主义的成果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阿塞拜疆民法典》第135条第3款和《瑞士宪法》第120条外加《联邦非人类基因技术法》的相关规定的贡献在于承认了植物享有权利,这是破除了非人类生命领域长期存在的动物中心主义的结果。
如前所述,马修·霍尔观察到:《圣经》考虑了动物与人的共性,没有证据表明《圣经》曾考虑植物与人的共性,这是宗教世界的预设。在世俗世界,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思想一直贱视植物,原因在于动物有与人相似的感官,甚至有脑,而植物与人没有这些相似性。这种倾向有人称之为大脑沙文主义,直到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之后才逐渐被破除。达尔文于1880年与其子弗朗西斯·达尔文(Francis Darwin,1848—1925)合著了《植物运动的力量》一书,首次探讨了植物的认知。他们使用神经学描述了植物根部的敏感性,提出根尖的作用类似于某些低等动物的大脑。此等根尖对感觉作出反应以确定植物的下一个动作。结论是:植物具有最低限度的认知,许多动物甚至细菌也具有这样程度的认知能力。
撇开非西方文化学者对植物地位的肯认不谈,在达尔文之后,不少西方学者研究了植物智力问题。
2006年,意大利学者斯特凡诺·曼库索(Stefano Mancuso,1965—今)等人(即埃里克·D.布伦纳、莱纳·斯塔尔伯格、豪尔赫·维万科、弗兰蒂塞克·巴卢什卡、伊丽莎白·范·沃尔肯伯格)发表《植物神经生物学:植物信号的综合观点》一文,说明了植物如何处理从环境中获得的信息,以最佳地发展、繁荣和繁殖的过程,从而证成了植物智力。曼库索等指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许多人错误地认为智力是“使我们区别于其他生物的东西”,但如果我们将智力视为解决和克服困难的能力,植物也拥有它,正是智力使植物发展并对它们在整个个体发生过程中遇到的大多数问题作出反应。植物有自己的智力形式,植物靠它们彼此沟通,还靠它们与动物沟通。最典型、最普遍的例子是,植物利用自己果实的香味吸引动物食用并排出种子来扩大自身的传播范围。当然,植物为了使种子能有效传播,让未熟的果实不能吃,这是一种保护机制。2013年,曼库索与亚历山德拉·维奥拉合作,把上述成果发展成了《灿烂的绿色:植物智能的惊人历史和科学》一书,扩展了其植物智力理论。两位作者证明,植物除了具有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听觉外,还有另外15种感觉。这样的论证直接否定了耆那教关于植物仅有触觉的说法。就植物的听觉而言,曼库索做过这样的实验:向某种植物发射200赫兹的声音,然后以高速摄影机记录植物的反应,发现植物能感受且“理解”收到的声音。植物能知晓电流、水流声等,与周边环境进行交流,靠声音来寻找合适自己生活的地方。总之,曼库索及其合作者的著作更新了人们对植物的认识。
2008年,弗洛里安·凯什兰出版《植物对话:偷听植物世界的秘密》一书。作者试图挑战植物都被视为机器,它们只是根据内置程序作出行为的成见。作者介绍,有大学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用最现代的方法研究植物的语言,有的学者甚至在植物中找到神经样结构。由此,作者成功地创造了新的植物形象。
2011年,美国学者马修·霍尔出版了《作为人的植物:哲学性的植物学》一书。此书回顾了西方文化传统中对非人类生命界采用动物中心主义的历史,以及非西方文明中一些有利于植物获得与动物同样关注的观点,并综述了达尔文以来的破除动物中心主义的理论,主张将植物看成主体(person),从而把现今人与植物的工具关系转化为尊重关系。先是减少人类对植物界的损害,进而修复已实施的损害。
2014年,英国学者安东尼·特雷瓦瓦斯(Anthony Trewavas,1939—今)出版了《植物行为和智力》一书,指出:学习、记忆和智力在植物学中不是常用术语,因为人们相信行为只是具有神经系统的生物体的特性。但有大量证据证明植物有智力。例如,有些植物通过撞击产生的机械刺激来探测合适的支障物;有些植物则利用反射的远红光或挥发性化学物质完成探测;它们还能预测未来在何处会遭遇竞争与被遮挡光线,如果有必要,就采取入侵行动,率先长出枝叶占领有利位置,让整个身体在阳光下获得最适宜的位置。植物甚至有神经系统,植物细胞之间的离子通道,主要是钙离子通道,就是其神经系统。特雷瓦瓦斯认为植物智力的用途之一是竞争。确实,像所有生物一样,植物必须获得它们生长所需的资源,它们需要应对捕食者、疾病并寻找配偶,还要争夺必需品、光、矿物质、水以及空间,具有尖端生长的分枝结构是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它为植物提供了占用最大空间、获取资源的潜力,反过来又有助于植物阻止附近竞争对手获得资源。
豌豆的智力受到学界的特别关注。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布劳斯坦沙漠研究所的一组科学家发表的研究结果证明,遭受干旱的豌豆苗会将其困窘传递给与它共享土壤的同类植物。换句话说,它通过根向其邻居传递关于干旱开始的生化信息,促使它们作出反应。那么,植物是如何传递信号的?所有植物的叶子、枝条、根、皮、果实和花朵都会释放挥发性有机化学物质,它们可能就是植物的语言。另外,豌豆还会铤而走险。为了实验,谢梅什博士和牛津大学行为生态学家亚力克斯·卡切尔尼克种植了一些豌豆,并将豌豆根部一分为二,放进两个花盆。其中一个花盆的营养含量是恒定的,另一个花盆的营养含量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当营养不足时,营养含量变化不定的花盆里的豌豆生出了更多的根;但当营养充足时,它们更倾向于营养含量恒定的花盆。这个实验证明:豌豆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冒险。
2013年,迈克尔·马德尔(Michael Marder,1980—今)出版《植物思维:植物生命的哲学》一书。作者笔下的“植物思维”指植物特有的非认知、非观念、非意象的思维方式,也可称为“无头思维”。非认知,指植物思维完全由遗传和环境决定,区别于具有认知性的动物思维。非观念也是相对于人的思维而言的。人通过感官接受刺激,将此等刺激输入大脑进行整理,形成观念。植物无大脑,所以其思维是非观念的。非意象,即无须视觉形象帮助。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前,人们大多认为思维靠图像的帮助进行,1900年左右,在德国维尔茨堡工作的一群心理学家证明,人们可以在无图像帮助的情况下思维,此种思维即非意象的思维。马德尔认为植物的思维属此。总之,马德尔超越了植物智力的言论,进入植物思维的言论,推动了植物类人化的进程。
2014年,我国学者祁云枝出版了《植物哲学:植物让人如此动情》一书揭示植物的智慧,例如揭示竹子具有团队精神,群生群长,相互扶持。此书让我国跟上了肯认植物智力的时代潮流,但与外国同道者比较起来,祁云枝的写作着重于外在观察,而不是内在“解剖”(例如证明植物有智慧的原因是有类似“神经”的组织),属于科普读物。
以上成果,打破了非人类生命界的动物中心主义,为植物受到法律更认真的对待提供了证成。这些成果是催生2000年的《阿塞拜疆民法典》第135条第3款的意识形态环境。《瑞士宪法》的规定似乎跟上述研究成果关联不大,更多出于一种宗教感和保守性。它的蓝本是更早的1980年《阿尔高州宪法》第14条:科学教学和研究以及艺术活动自由。教学与研究必须尊重被造物的尊严。蓝本诞生的时间早于几乎所有的证成植物主体资格的科研成果的发表时间,所以人们把《瑞士宪法》中的有利于植物的规定归因于宗教情怀。但在2008年,瑞士联邦伦理委员会发布了一份针对非人类的生物技术的《关于作为生命体的植物的尊严的报告》,其中指出:“植物生命不仅应该得到所有其他生物的尊重,而且还具有绝对的道德价值,不能简化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加强保育的对象了事。”从此以后,让植物遭受“任意伤害”将在道德上受到谴责,而将植物工具化处理需要道德上的正当理由。例如:一个农夫为了其牲口果腹而打草是可接受的行为,在打完草回家的路上,他无理由地用镰刀割了些野花,这个行动很可能就是不道德的。这个文件建立在大量的证成植物主体资格的文献基础上,为《瑞士宪法》第120条补上了科研基础。
最后要提到的科研成果是美国法学家克里斯托弗·斯通(Christopher Stone,1937—2021)于1972年发表的文章《树应该有诉讼资格吗?迈向自然物的法律权利》,此文率先提出了自然物或无生命体的法律权利和诉讼资格的主张:既然法律可以赋予不能说话、没有意识的国家、公司、婴儿、无行为能力人、自治城市和大学等法律主体资格,可以为它们申请保护人或代理人,为什么法律不能赋予自然物体以法律主体资格,不能为它们申请保护人或代理人呢?此文并未研究植物智力问题,但主张植物主体化,尤其体现在其标题中,所以笔者认为它也是去动物中心主义的重要文献。
五
植物的民法地位重整
如前所述,《发现植物:关于植物权利的莱瑙论文》确立了6项植物权利:生殖权、自主权、进化权、作为种的幸存权、在研究和开发中的受尊重权、排斥专利化权。它们都是对抗权力的傲慢的权利,如同瑞士的经验所证实的,它们大多不宜写入民法典。那么,在民法中应如何体现上述学界对植物的新认知呢?
首先要说的是,世界现有的植物种类超过40万种,对它们一概而论是不科学的。俄罗斯学者埃皮凡诺娃(T. B. Епифанова)等人对作为民事权利客体的植物进行了分类,把它们分为自然栖息的和被孤立的两大类。前者包括:(1)濒危植物。列入国际红皮书中的植物;列入俄罗斯红皮书中的植物;特别保护自然区域(国家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自然公园、自然纪念碑、树木公园和植物园)中的植物。(2)属于采集对象的植物(蘑菇、药用植物的浆果、花、草和根等)。(3)处于自然自由状态的植物及未被一般规则定义为客体的植物。后者包括:(1)农业植物。(2)转基因植物的母本。(3)转基因植物。(4)观赏植物。(5)药用植物。
笔者理解的是,在这样的分类中,自然栖息的植物是自由植物,人类通常不宜侵犯。被孤立的植物是人类的劳动对象,人类可带着尊敬利用。如果这一理解未错,可以说,埃皮凡诺娃等人的文章继续了《阿塞拜疆民法典》第135条第3款开创的问题,并把它具体化了。
在被孤立的植物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农业植物的民法地位重整。它们的数目不多。据研究,人类的主食主要包括14种栽培植物,而人类消耗的80%的卡路里来自6种植物:小麦、水稻、玉米、马铃薯、红薯和木薯。问题在于,既然农业植物也有生命,人类能否吃它们?
1993年的《全球伦理普世宣言》承认人类比非人类具有较大的内在价值,所以,用植物和动物果腹是更大的善,为此可以毁灭自然形态的生物。
马德尔在其文章《吃植物合道德吗?》中指出,问题显然不是“我能吃植物吗?”而是“我怎么吃植物?”,应该是带着尊敬去吃,有节制地去吃,不浪费。
1994年在法国诞生的《树木权利宣言》第5条也规定:为了满足人类的需求,一些树木被种植然后被利用,不能成为受保护的树木。但人们在利用森林或农村树木时,必须考虑树木的生命周期、自然更新的能力、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此条承认并非一切树木都享受古树名木的待遇,但树木监护人要合理利用之。至此,我们可把《阿塞拜疆民法典》第135条第3款的规定具体化一下:自由的植物不是物,孤立的植物还是物,但人们要带着尊敬利用之。
带着尊敬利用,是课加给植物所有人的义务,除了不浪费,还要承担以下责任:第一,要保护古树名木,也就是放弃对它们的经济利用可能,维持其生态功能;第二,在为经济目的“杀死”一棵树后补种同样数目的树;]第三,当树木自然消失时,土地所有者应根据物种档案的要求在一年内补种;第四,不实施可能导致树木过早枯死的行为;第五,浇水;第六,不滥用树木所有权。这6项规定,还是对作为所有权客体的树木的保护,实际上否定了树木的主体资格。从瑞士的经验来看,植物的尊严权属于公法规定,如果我国的公法或私法承认植物的这一权利,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23条中作为知识产权之一的植物新品种权将受到冲击。有人认为,植物新品种权是一种强加于发展中国家的知识产权形式。该权不是保护品种,而是保护大型植物育种和生物技术公司的利益。通过这种方式,育种者被肯认为植物新品种的创造者,就像版权和专利被看作授予作者和发明家的荣誉一样,育种者被授予植物新品种权。这意味着种植新品种植物(PVP)的农民被禁止出售他们从作物中收获的种子,而且越来越多的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成员国禁止在非商业基础上保存和交换种子。这也意味着农民每次购买种子都要支付特许权使用费。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从狭义和广义上都否定了农民的权利。从狭义上讲,农民自由保存收获的种子的权利受到限制。从广义上讲,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不承认或支持社区对生物多样性及其创新空间的固有权利。而按我国投赞成票通过的《联合国农民和农村地区其他劳动者权利宣言》第5条(种子及传统农法的权利)的规定:农民有权决定种植的种子品种;农民有权拒绝种植其认为在经济、生态和文化上有危害的植物品种;农民有权拒绝工业化的农耕方式;……农民有权以个别或集体的方式选择其生产的作物和品种,以及从事农、渔、牧相关活动的方式;……农民有权栽种并培育自己的品种,并有权交换、赠予或销售这些种子。为了维护农民的此等权利,李昌平发表《给农民留几粒真正的种子——致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另外,植物新品种权可能与《生物多样性公约》(1992年)第10条的这部分内容冲突:“每一缔约国应尽可能并酌情:……(二)采取有关利用生物资源的措施,以避免或尽量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三)保护并鼓励那些按照传统文化惯例且符合保护或持续利用要求的生物资源习惯使用方式……”植物新品种权构成对生物多样性的不利影响,并不利于保护并鼓励那些按照传统文化惯例使用生物资源的方式。所以,如果植物的尊严权理论得到采用,植物新品种权的存废将成为探讨的问题。
六
植物法律地位另类入宪与我国《宪法》中的植物条款的应有调整
如前所述,瑞士已完成植物法律地位入宪,还有一些国家以不同的方式完成了植物法律地位入宪,我国为其中之一。1982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法》)第9条第2款规定: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保护珍贵的动物和植物。该规定课加国家保护珍贵动植物的义务,反言之,不珍贵的动植物得不到这样的保护。尽管该款不讲求平等,却是我国动植物地位宪法化的初次尝试,因为我国的1954年《宪法》、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均无这样的规定。此等规定之纳入,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的影响有关。该联盟1948年成立于法国,从1966年起,它开始出版濒危物种的红皮书和红色名录,以促进成员国对名录中所列的物种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前文提及的埃皮凡诺娃等人的文章就提到了植物方面的俄罗斯本国红皮书以及国际性的红皮书,后一种红皮书当出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之手。该联盟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在我国开展工作。受其影响,1982年7月,当时的国务院环保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组织召开了有关单位参加的中国植物红皮书编写会议,并正式成立编辑组。1982年12月4日,前引《宪法》第9条第2款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诞生。10年后的1992年,《中国植物红皮书》第一册正式出版,对何谓“珍贵植物”问题作出了部分解释。这个“第一册”列举了388种植物,其中一类保护植物8种,二类保护植物143种,三类保护植物222种。说它是“部分解释”,乃因为在笔者写作本文的2023年10月,“第二册”仍未出现。继之,1999年8月4日,国务院批准了国家林业局和农业部发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该名录共列植物419种,真菌3种,虫草为其中之一。由于篇幅有限,本文略过省市级的和行业性(例如药材业)的野生植物保护名录不提。这些名录使我国《宪法》第9条第2款关于植物的规定具体化。作为一个整体,它们的特征有:其一,从作为国家所有权客体的自然资源的一种的角度规定植物,而非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规定;其二,只关注野生植物和野生真菌,不关注农业植物以及其他高度卷入人类生产生活的植物和真菌,因为它们并不属于作为国家所有权客体的自然资源,也不珍稀;其三,只关注列入名录的植物免于灭绝,而不关注针对此等植物的基因操作。所以,我国《宪法》第9条第2款虽并非关于植物法律地位的综合规定,但具有一定的民法意义。2003年的《乌克兰民法典》第180条规定:“……3.红皮书内列举的动物只有在法律规定的情形内并按法律规定的程序才能成为民事流转的客体。”此款说的是红皮书列举的动物是限制流通物,类比过来,《中国植物红皮书》等官方文件中列举的植物也是限制流通物,不在红皮书的名单中的植物可自由流通。
从1982年到2024年,时间过去了42年,在此期间发生了许多改变。其一,1992年瑞士修宪增加植物法律地位规定,它说明,人类对野生植物的灭绝的关注保持不变,但增加了对农业植物和其他“人化”植物蒙受鲁莽的基因干预的恐惧。其二,2000年《阿塞拜疆民法典》第135条第3款采用植物非物的规定。其三,玻利维亚于2010年12月21日颁布了《地球母亲权利法》,其第3条(地球母亲)规定:地球母亲是由所有生命系统和生物构成的不可分割的动态生命系统,它们相互关联、相互依存、相辅相成,属于同一命运共同体。此条未明言的植物和动物包含在“所有生命系统和生物”的一般表述中,它们是构成地球母亲的要素。其四,智利2022年9月4日欲以一部生态宪法取代旧宪法,草案凡388条,其中98条直接或间接与环保有关。其第103条和第127条承认自然为权利主体。这个“自然”是“地球母亲”的别样表述,其中包括植物和动物。第148~150条设立了自然保护机构。该机构是自然这个主体的监护人。这一生态宪法草案尽管未通过全民公决,但它仍向我们揭示了当代宪法发展的生态方向。其五,也是最重要的,我国政府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了从环境保护到生态维护的转型,最好的例证是我国在已定每年的6月5日为全国环境日的前提下又定每年的8月15日为全国生态日,两日同设表明设环境日不能解决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问题,必须设生态日“补火”。环境日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此等主义表现为把人之外的一切都当作客体,而生态日是生态中心主义的,此等主义的要旨是承认所有地球生命的主体地位,由此承认人类与其他地球生命的和谐共生。要指出的是,生态日的设立不过是一个小高潮而已。2007年的中共十七大报告就提出建设生态文明,这是一种超越工业文明的更高级的文明。2020年12月26日,我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其第1条规定:为了加强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促进资源合理高效利用,保障生态安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制定本法。其第3条规定:长江流域经济社会发展,应当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长江保护应当坚持统筹协调、科学规划、创新驱动、系统治理。两个条文中的“保障生态安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是“生态文明”的体现。2022年12月30日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条也有同样体现:为了保护野生动物,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制定本法。此条中的“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表述尤其具有生态性。
基于这些变化,我国《宪法》中的植物条款有了修订的需要。建议在适当的时候修改之。首先,要把它改造成一个从环境保护出发的规定。目前笔者查到的规定植物法律地位的宪法共有6部,除《瑞士宪法》采取确立植物尊严权角度外,《巴西宪法》(1988)、《立陶宛宪法》(1992)、《阿塞拜疆宪法》(1995)、《玻利维亚宪法》(2009)、《吉尔吉斯斯坦宪法》(2010)都采取环境保护的角度。例如,《巴西宪法》第225条第7款这样规定:保护动植物群,依法禁止一切危害动植物群的生态功能、导致物种灭绝或者虐待动物的行为。又如,《立陶宛宪法》第54条这样规定:“1.国家应当保护自然环境、野生动植物、自然个体和特殊价值地区,监督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其恢复和增加;2.法律禁止破坏地球和地下土壤、污染水和空气、对环境造成放射性影响以及破坏动植物群。”借鉴这些立法例,笔者建议把我国《宪法》的第9条第2款移到第26条的位置并在经一定修改后与其合并。其次,要把它改造成一个考虑全部植物(野生的和“人化”的)的规定和一个全面考虑植物的命运的规定,遭受灭绝诚然不幸,遭受基因篡改,变得不是它自己,尽管得以生存,也很难说是“幸”。按这样的要求,我国《宪法》的第26条应如此行文:1.国家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2.国家保护动物和植物,禁止对它们实施任意的基因操作;3.国家组织和鼓励植树造林,保护林木。此条的第2款是第9条第2款的转化形式。“转化”一是表现为移位,这一移,意味着此条不仅保护国有的动植物,而且也保护集体所有和个人所有的动植物;二是表现为去掉了“珍贵”两字,由此可包含非珍贵的野生植物和农业植物;三是表现为借鉴《瑞士宪法》第120条,增加了反任意的基因操作的规定。此款未明言植物是主体,但暗含植物具有基因自主权的意思,国家被设定为此等主体的监护人,但国家为抽象的存在,必须有具体的机关或个人实现国家的意志,检察院为这样的机关之一。到目前为止,我国检察机关已提起保护珍稀植物的公益诉讼不少,证明此等机关可被考虑为植物主体的监护人。
七
结论
综上所述,《阿塞拜疆民法典》首次从私法角度把植物去客体化,打破了非人类生命界的动物中心主义,其积极意义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把所有的植物都去客体化有些过火,埃皮凡诺娃只让自由植物去客体化,而把为数有限的孤立植物保留在客体的范畴内,并对利用它们课加了限制。瑞士则从公法的角度规定植物的权利,尤其是其尊严权。两种处理,殊途同归,都达成了对植物法律地位的重设。
植物主体化是民事权利客体非生命化的第二步,第一步是动物主体化。如果把民法客体的去生物化看作一种趋势,民法客体的去生物化的最后一步应指向真菌和微生物。《瑞士宪法》第120条提到了其他生物,应该指的是真菌和微生物。这可算作立法者以并非明示的方式考虑到了真菌和微生物的法律地位的立法例。我国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第一批)》也不甘落后,把3种真菌列为保护对象。尽管动物和植物都是上述趋势的作用对象,但两者主体化的原因有异。动物之所以被主体化,乃因为它们与人结构类似,尤其在有大脑上类似,并且由于动物可借助声音表达喜怒哀乐,人类比较了解动物。植物被主体化的原因则相反,在于我们不了解植物,由于它们与我们有太多差异,尤其是无脑,且不能用声音表达,人类出于少知多畏的情怀赋予植物权利,以防止各种新生的生物技术的滥用。
植物有40多万种,它们并非等同地受到法律的关注,树木受到的关注最多,为它们诞生了两个权利宣言,暂未看到其他植物赢得专项宣言的报道。所以,植物在法律的眼里也有“贵族”和“平民”之分,树木整体上处在贵族的地位,但在其内部,又有贵贱之分。例如,同属于芸香科植物,枳通常被作为桔的砧木使用,代桔吸收养料水分,自己难见天日,套用前引《树木权利宣言》第1条的表述,桔生活在大气中,枳生活在地下。前者是目的,后者是手段,所以,后者是前者的“奴隶”。人对两种同科植物的关系的这种安排侵犯了枳的“尊严”,因为在此等情形,枳并非为自身而存在,而是直接为桔、间接为人类而存在。所以,植物主体化的落实,会导致既有的一些植物彼此间关系的重整。
植物的主体化是民事主体“扩容”的一部分,被扩进来的有生物和非生物,后者如河流,被扩进来的理由是值得保护的利益。就被扩进来的生物而言,产生了寻找把它们扩进来的理由的问题。在单纯以人为主体的情况下,主体的标准是理性的拥有。把动物扩进来的时候,找到的主体标准是感觉,对动物的新界定“有感生灵”隐含着这样的标准。在动物的主体资格论证中,无人谈论动物的智力问题。从本文可见,学界在论证植物的主体资格的时候,采用的标准是智力。所以,在非人类生命主体化的论证中,存在标准不一的问题。那么,有无必要寻求统一的主体标准呢?如果有必要,可否把非人类生命的主体标准也界定为理性呢?因为智力是运用理性的条件,如果无脑的植物都有智力,有脑的动物更有。但是,理性不过是主体实施法律行为的条件,如果非人类生命尽管有理性(虽然这样的理性低于人类的理性),但不能自行实施法律行为,这样的理性也没有什么意义。所以,在确定非人类生命的主体资格时,我们还是坚持匈牙利学者亚历山大·内卡姆(Alexander Nékám,1905—1982)的利益说为好。斯人著有《法律实体的人格的概念》,主张以“法律实体”的概念取代自然人(person)、法人(corporate person)、权利主体(subject of rights)的概念。内卡姆反对自然人概念的原因是它被用来指称人类。反对法人概念的原因是该概念是对自然人的概念的攀比。而法律实体是一个被动的、抽象的、人为的概念,除了与抽象的法律权利相关外,没有任何意义。按照这一理论,只要是值得法律保护的利益的载体,无论它是否有生命,以何种方式存在,都是法律实体,从而享有人格。实际上,自然主体化最重要的主张者克里斯托弗·斯通也是这么想的,其划时代论文的题目就是《树应该有诉讼资格吗?迈向自然物的法律权利》,这个题目表明作者主张树是诉讼主体的立场,但斯通并未对树具有智力提出论证,因为这是不必要的,树是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够了。所以,斯通之后的许多学者提出的植物具有智力的论证,不过是在主体资格赋予上拟人的余迹,或反对动物中心主义而已,可看作冗余的论证。总之,非人类生命体的生存,是值得保护的利益,如同自然的健全维持是值得保护的利益。所以,有理性的非人类生命和无理性的自然的主体化理由实际上是一样的。然而,尽管非人类生命进入主体范畴的过程就是去人类中心主义的过程,但在这一过程中人们还是发现,人类确实在各个方面(尤其在头脑方面)都居于优越的地位,但此等地位切不可滥用,而应用在照管非人类生命主体和自然上。
接下来要讲到的是有害植物是否要像其他植物一样取得主体资格的问题。暂未看到关于有害植物主体资格的讨论,但看到了关于是否要消灭有害动物蚊子的讨论,结论是蚊子有清除废物、传播花粉、作为鱼类的食物等积极作用,不可完全消灭。可以把对蚊子的这些肯认移用于所谓的有害植物,它们的积极功能也许我们只是暂未看到,但我们应相信“每物必有其用”的箴言。
最后回答本文标题提出的问题:植物是什么?答曰应该是主体。或问,为何非要把动物和植物主体化,把它们当作特殊的客体不行吗?斯通在其划时代论文中考虑了这一问题,答案是把包括动植物在内的自然物主体化的原因是避免它们被其所有人出卖。例如,我的土地被你污染,你给我很好的赔偿,我满意之并迁居他地,而牺牲了我原来土地上因为污染被杀死的动植物。相反,把动植物作为主体,侵权人不仅要赔偿我,而且要恢复它们。斯通举了这样的例子,假设一个海胆群落被毁,如果在此等群落的原来栖居地恢复它们不可能,则要在地球上的其他某个地方重建一个海胆群落。当然,摆脱植物不过是特殊客体的推理的有力安排是让植物也承担责任,斯通未直接考虑过这一问题,但考虑了包罗更广泛的自然物的此等问题。他问:河流侵权了怎么办?河流淹死人,不停泛滥并且毁坏庄稼,或者森林燃烧,向邻近的社区纵火怎么办?如果建立了信托基金(通过让自然物累积他人侵害它的损害赔偿金作为自己的损害赔偿金),就可以利用它们来满足针对自己的不利判决,使自然物承担其对其他权利持有者所造成的某些危害的成本。此论可套用于植物。按照我国《民法典》第1234条和第1235条的规定,侵害生态环境者要承担生态修复费用。被侵害者是植物的情形,此等费用在完成修复后有剩余的,可成为上述信托基金的来源。人类利用植物获得的利益,也可拿出一部分投入此等基金,当植物(例如森林)自燃致人损害时,此等基金可用来赔偿受害人。所幸的是,植物由于其不动性,致人损害的可能性比动物和河流不知小多少,所以,上述基金的存在必要性很小。当然,上述安排看起来粗糙,但哪个新事物诞生时不是粗糙的呢?每个新事物都是在实践中改进自己并达至完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