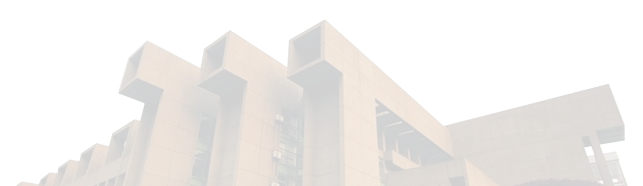我和湖大法学院的情缘

邓祥瑞(44118太阳成城集团荣休教师 湖南醒龙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
(一)
日子好不经用,转眼间,我从湖大法学院退休已经大半年了。去年9月教师节刚过,学校人事处便通知我去填写了诸多表格;没多久,离退休处又通知我去领了纪念品。签领的时候,我看到一份学校的退休文件,上面有我的名字。再后来,社保卡取代了工资卡,我领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退休金。流程很简单,一气呵成,几乎是在悄无声息中,我完成了自己身份的转换。
退休,无疑是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有人对此讳莫如深,也有人会心态失衡。朋友中不止一个先我退休的党政机关干部,曾言之谆谆告诫我,退休后除非必要,尽量少去原单位露面。我不以为然,但凡去河西,都会尽量去法学楼转转,海来阿木式的,“只是见一面”。
亮出校园卡,把车开进校内的停车坪,依然没有违和感;进得大门,认识不认识的学生,都会道一声“老师好”,我则习惯性地回以蒙娜丽莎式的微笑;遇到的同事和门卫师傅会热情地打招呼,偶尔也有不知情的老师,带着讶异的表情,惊问一句“邓老师,你怎么就退休了?”令我心情瞬间美丽,很享受这种“貌似年轻”的慰藉。
前几天,我又回了一趟法学院,这次是去接受大二学生的采访。同学们的访谈活动冠名为“读懂中国”,起初我觉得太“高大上”,没敢贸然答应。细问之下,知道她们想让我谈的,是我眼中的法学院以及我在法学院的过往,才勉为其难,在细雨霏霏中赴了约。访谈一开始,我就察觉到,同学们做足了功课,知道我在进入湖大法学院之前,已有了在其他单位17年的工作经历,也知道我在教师之外一直有一个刑辩律师的身份。访谈中,她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契机与湖大结的缘,让我开启了记忆的闸门。
(二)
同学们用了“契机”一词。是的,我自己的经历表明,人生可以选择,也有机缘。
我是1981年考的大学,填报志愿时,我很茫然,不知如何下手。当年,母亲所在的祁阳电机厂,启用了一位60年代的老大学生做厂长,他建议我学法律,说是拨乱反正后,国家会重视法制,需要大批的法律人才。于是,我填报了武汉大学法律系,结果误打误撞读了所名校,也注定了一生的职业轨迹。
1985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湖南省公安厅,在政治部从事文秘工作。大概过了两年,当初的警服诱惑已经消退,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喜欢机关“文山会海、品茶读报”的生存模式,并开始担心自己的专业日渐荒废,萌生了改做一名法学老师或者做一名律师的想法。现在回过头想,除了对专业的珍视,希望获得更多的个人自由,也是我如此企划的原因。
1987年,我曾经有机会去湖南公安专科学校(警察学院的前身)教书,因为领导不放行而失之交臂。第二年我咬牙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了全套资料,紧锣密鼓地备考一个月,通过了第二届全国律师资格统一考试。
1993年春末夏初之际,我终于打定主意,离开了工作8年之久的湖南省公安厅,调入湖南省贸促会法律部,在省司法厅、外经委、贸促会联合开办的湖南国际经济贸易律师事务所开始了我的律师生涯,时年30岁。
这在当时是一个大胆而冒险的决定,意味着离开了“舒适圈”,前途未卜。我家上下两代人都不乐意,家父反对的原因,是他寄希望于我在这个“官本位”根深蒂固的国度“学而优则仕”;而年仅3岁的儿子,则是习惯了我那一身“83式”橄榄色警服带给他的安全感。不少朋友也为我惋惜。若干年后,我才意识到,真正认同我的,可能要数后来我在看守所会见、闲聊过的失意官员。
两年之后的1995年,我再次异动,调入省社科院法学所,参与创办了现在的湖南日月明律师事务所。其后的7年,是我作为一名律师的重要成长阶段,接办了一系列大要辩护案件。
2002年,从武大学成归来、已在湖大法学院担任副院长的孙昌军博士,向我发出邀约,希望我到法学院任教。接下来,刘定华院长、韩红书记、屈茂辉教授、余松龄教授等,听了我半个小时的试讲,然后接纳了我。那一年,我39岁,已经人到中年,脸上只残存了不多的胶原蛋白。
(三)

从2002年8月报到,到2023年9月退休,我在湖大法学院工作了整整二十一年。抚今追昔,我对湖大法学院充满了感激之情。庸常如我,素无大志,年轻孟浪之时心仪的两个职业,最初的心愿是“卧龙凤雏”得一足矣,因为我湖法学院成全,让我在律师之外,又圆了教师梦,何其幸哉!
在湖大法学院二十一年,经历了很多事,结识了许多良师益友,见证和参与了她的发展壮大。有人说,男人是慢慢长大的。漫长也短暂的二十余年,也是我不断成长的过程。海量的回忆无法尽述,但我对法学院有两点感受,鲜明而强烈,不妨一提。
首先,这是一个和谐、友爱的集体。初入法学院,因为之前就与不少老师相熟,我没把自己当外人,很快就融入了集体,也很快感受到了同事之间十分轻松和融洽的氛围。大家管刘院长叫“刘头”,管王远明副院长叫“王头”,每当聚集在一起,总是欢声笑语,彼此常会开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我在好几个单位待过,对这种相对简单的人际关系,特别有感觉,也特别喜欢。学院在假期还经常组织教职员工旅游,我记忆中去过泰山,还去过湘西洪江古城;年头岁尾,会组织全员聚餐,家属和“教二代”也参与其中,俨然一个大家庭,其乐融融。后来学院从财院校区搬到南校区,人员不断增加,情势也有了变化,这种集体性活动也就减少了,加上老师们的科研压力越来越大,神情变得凝重,欢快的气氛有所减弱。但同事们之间自然、亲切、友善的关系总体上被传承了下来。
另外一个比较有感的,是法学院的领导不摆架子,没有官气。最早掌门人刘院长的谦和、包容有口皆碑,其后的历任院领导,基本上也是平和、低调,不以管人者自居,尽显法律学人的底蕴。屈院长与我年龄相仿,我多数时候叫他“茂哥”,别的同事也常常如此称呼,很少称他院长。骆之书记比我略小,我一直喊他“骆之”,只是某个特定时段故意称他“书(输)记”,不容他不接受。他曾在学校中枢任事,同事在学校有事爱找他帮忙,他是能帮尽帮。四奇院长也是如此,见面时总是称我为师兄,小眼睛里满是笑意。曾任院长杜钢建老师,退休之后对人种的起源、迁徙等常有惊人之论,被奉为新儒学代表人物,有“战狼学者”之称,令人不明觉厉。但他在法学院的6年,平心而论,留给我的是“谦谦君子”的形象。
我在法学院二十一年,曾挨过一次批评,因为某年支部换届时不愿担任支部书记。当时的书记陈宇翔教授很注意方法,没有点名,而且那天我正好不在会场。陈书记是个性情中人,为人正直,还曾下水救人,是我心目中很好的领导。
(四)

作为一名退休老师,我也回顾了自己这二十一年。说来惭愧,二十余年来,我对法学院贡献不多,可以说是乏善可陈。
先得感谢学院,二十一年来,我一直没有中断律师执业,虽然是兼职,虽然律师实务中获取的素材也有利于我的教学,但毕竟是我的“副业”,也多少会分散我的精力,尤其是影响到对学院来说十分重要的科研工作。我感谢学院领导和同事们的支持与包容,感谢教务部门老师在课程时间安排上给予的关照。值得欣慰的是,近二十年来,包括已故的邱兴隆老师、先后离开学院的罗智勇、段启俊老师和我本人在内,在刑事辩护领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展现了湖大法律人应有的风貌。
我当初是为教书而来,教学是我喜爱的事业。这些年来,我先后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过律师制度和实务、犯罪学、证据法学、刑法学、刑事司法实务、法律谈判等课程。在整个教学生涯中,我给自己确立过如下几项原则:教学优先,律师业务不能影响授课;理论联系实际,尽量让授课内容生动;教书与育人结合,尽量多传授有用的知识,拓宽学生的视野;贴近现实,讲真话,不打诳语,避免误导心智成长中的学生。自我感觉,我的课堂是轻松的,不枯燥的,经常会传出笑声。这得益于我律师工作练就的口才、长时间的实务积累以及我固有的幽默感。当然,幽默感这东西挺珍贵,有没有我并不是太自信,也就这么放胆一说。
(五)
教书让我快乐。关于这一点,在退休之前,我是偷着乐,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大概7、8年前的一天,我接到一个深圳打来的电话,对方自报家门,告诉我他是法学院早年的毕业生,现在在深圳做律师。本次联系我,是要把一个湖南的案子推荐给我。在电话中,他特别提到,当年是因为听了我的律师课程,才选择律师职业的。最后还郑重地道了声“谢谢老师”。这件事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老师的教学会很直接地影响到学生,包括人生和事业。当然,这件事也让我深刻地意识到老师的责任,同时滋生出成就感和自豪感。更多的同学,多年之后还记得我随身携带的大号茶杯,这些细节让我莫名其妙地兴奋与满足。
善待学生,是我坚守的信条。疫情之前的许多年,我自己带的学生,几乎都曾到我家做过客。不少毕业后回长沙的同学,也享受过我的家宴。湖大学子在长沙做律师的不少,给人的感觉是,“到处都是我们的人”。但凡有学生提出业务上的问题,我都会认真地作出解答。
与学生相处,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平等相待。我就曾经很郑重地给学生道过歉,只是这个道歉来得有些迟。也是刚入法学院那几年。有一次期末考试,律师实务课程有一道开卷题,是给出一个刑事案例,要求同学们写一份辩护词。结果阅卷时,我发现有两份挨在一起的答题纸上,辩护词的开场白基本雷同,而且都把宪法规定当作出庭辩护的依据,而置刑诉法于不顾,错的也一样。这两个同学一男一女,考试时正好坐在前后排。我当即认定他们作弊,必有一人抄袭,遂把他们通知到办公室,痛批一顿,把女同学都整哭了。他们解释过,因为是开卷,他们是模仿一本书上的辩护词写的,我当时根本不容他们分辩。几年后,我偶然发现了他们讲的那本书,一本律师制度恢复初期的劣质出版物,才知道所谓抄袭是冤枉了他们。又过了数年,我跟他们有了联系,发现他们并没有记恨我,相反觉得我指出他们写作上的错误对他们有益。有一天,他俩请我在阿波罗广场的“徐记”吃饭,我带了一瓶酒去,席间很正式地向他们道了歉,师生之间相谈甚欢,至今一直未中断过联系。
(六)
可能值得一提的事,是我指导学生竞赛曾经取得过一些成绩,算是为学院争过光。实话实说,学生竞赛的成绩,主要取决于学生的自身素质、赛前的准备和求胜心。我多年从事学科竞赛指导工作,许多时候成绩并不理想。
可以说说的,一是2008年我和袁坦中老师带队去北京参加“理律杯”竞赛,取得过第三名。这是全国法学类本科生的顶级赛事,参赛的都是名校,进入前三,已经是一个巨大的荣誉。这个成绩是坦中老师为主指导的,我只是与有荣焉。二是2017年我指导的全省法学研究生案例大赛,斩获了言词辩论赛冠军、最佳辩手和两项书状竞赛一等奖。这次比赛参赛的队员竞技水平高,求胜心强,赛前持续挑灯备战,相关学科的老师也给予了大力支持。

我曾在备赛阶段,从家里拿了核桃和甜橙,送到集训现场给队员们补脑。夫人发现存货锐减,心生疑窦,直到赛后才从学生写的公号文章里知道真相。她一边大呼“家贼难防”,一边又让我把全体参赛队员请到家里大快朵颐,也算是一个赛事“小花絮”吧。三是2019年、2021年指导研究生在徐州师范大学连续两届拿下了“玉龙杯全国高校模拟法庭大赛”法官组冠军和最佳法官称号。这项赛事我倒是颇有心得,诀窍就是让学生表现得更像真实的法官。我私下里曾想拿下三连冠,只可惜去年赛事未如期举办。当然,“胜败兵家事不期”,竞赛重在参与和历练,输赢并不是那么重要。

(七)
拉拉杂杂写了许多,碎片化,也杂乱无章。实际上,我想表达的就是我的感激之情。感谢法学院,给了我一个从教的机会;感谢同事们,给了我一个人际关系良好的工作环境;感谢我曾经教过的同学们,给了我许多美好的回忆。所有这一切,让我的人生充盈而丰满。
还有就是不舍和抱歉。我想,如果能像教员描绘的那样,“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一定会做得更好。现在能做的,就只有心底里无尽的祝福了。
转自 | 醒龙法律人